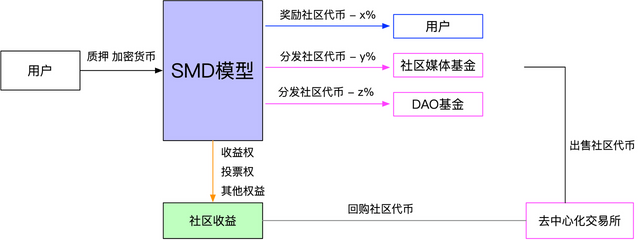有關同源詞研究的一點思考
董秀芳
0、引論
“同源詞”或稱“同源字”、“字族”、“詞族”,是指在發生學上有共同來源因而在音義兩方面都互相關聯的詞。同源詞的研究原屬於傳統的訓詁學研究的領域,本文試圖用現代的語言學觀念來重新審視同源詞問題。
1、以往研究中提到的“同源詞”的異質類型仔細分析,以往研究中提到的同源詞實際包含以下這些類型:
意義完全相同或只有細微差別的同源詞
這又分爲兩種情況:
A.音義皆同,這種情況可能只是字形的不同,實爲一個語言單位。這種情況王力(1982)已經指出。如:“欺”和“諆”、“胡”和“鬍”(鬍鬚)、“馭”和“禦”(在表示使馬的意思上完全相同)等。這一類與詞源研究以及詞義引申都沒有關係,不具有太多的語言學研究價值。把這些字歸爲同源字,只在梳理漢字的脈絡上有意義,屬於文字學的範疇。
B.意義完全相同,或只有細微差別,但語音不同。
這可能是由方言的差異造成的,如“遙”和“遼”、“改”和“革”等。
也可能是歷史音變造成的,如“母”和“媽”、“父”和“爸”等。
當然方言變異和歷史音變也是相通的,不過一個著眼于共時差異,一個著眼于歷時演變。
王力(1982)將“饑,饉”系爲一族,以爲它們意義相近,有見群旁紐、微文對轉的音轉關係。
張博(2003:96)又補充了五組相似的音轉關係對此加以驗證,認爲它們也都是同族詞:
璣:瑾 《說文》:“璣,珠不圓也。”“瑾,瑾瑜,美玉也。”
僟:謹 《說文》:“僟,精謹也。”“謹,慎也。”
幾:近、僅 《爾雅釋詁下》:“幾,近也”。段玉裁《說文解字》“僅”字注:
“唐人文字,僅多訓庶幾之幾。”
譏:靳 《說文》:“譏,誹也。”《左傳·莊公十一年》:“宋公靳之”杜預注:
“戲而相愧曰靳。”
覬:覲 《玉篇》:“覬,見也。”《爾雅釋詁上》:“覲,見也。”
上述音轉(實際上在沒弄清楚其性質之前,音轉只能看作是對詞之間的語音差別的描寫),並沒有帶來意義上的改變(有些例子在意義上只有細微差別)。
既然意義沒有變異,那麽這種音變就不與義變相連,就不屬於派生新詞的方式,而只是一種單純的語音變異。
這種音變究竟是同一方言語音系統的歷時演變還是不同方言的語音變異,這不屬於本文要關心的內容。
B 類對於重建原始語音形式是有意義的。
語音完全相同,意義不同但相關的同源詞,可以分爲兩種情況:
A、造詞時理據相同。如“兼,縑,鶼,鰜”,語源義都是兩者並存;“霞、蝦、
瑕”,語源義都是紅色;“杈、汊”,語源義都是分支等。
在這種情況下,同源詞中的成員可以是同時出現的,不存在歷史上的先後關係。
也可以在産生上有相後關係。即後來的概念因與先已存在的詞相近,而採用相似的音。這種一音對多義是由於客觀物件的相近,因此在命名時選擇了相同的語音形式。
B、是詞義引申的産物,造成的是一詞多義,但在後來新的義項用新的字表示,一詞多義分裂成不同的詞。如“魚、漁”等。
(3)音義都不同,但有關聯。這種音義之間的聯繫有可能是原生性的,是並立的。
也可能在出現時間上存在先後關係,具有源流關係。
我們關心的主要是第二類和第三類同源詞。從這些同源詞中可以發現詞義引申規
律,探求古代漢語的概念網路,尋覓古漢語的詞之詞之間的音義關聯模式。
2、隱喻和轉喻的不同作用
隱喻基於相似性,轉喻基於相關性。我們發現,由隱喻和轉喻這兩種機制所造成的詞義變化有不同的表現。
在隱喻基礎上形成的新的詞義一般構成的是一詞多義,並不産生語音上的變化。
語言一般不用詞法手段來表達隱喻義。比如,以下詞中隱喻義都與原義並存,成爲一個多義詞的不同義項:
頂:1 頭的最上部;頭頂。
2 物體的最上部。
鑽:1 鑽穴穿孔。
2 深入地探究事理。
遠:1 空間或時間的距離長。
2 某種差別程度大。
可以說,隱喻對於新的詞義(包括語法性意義)的産生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對於
新的詞的産生作用並不大。
有些隱喻義可能用新的字形來表示,但字音保持不變。在後代由於不瞭解其間的
關聯,就被看作是兩個詞了。這在同源詞中有顯示。如(以下幾例引自王力1982):
眉:1 眉毛,生於眼眶上緣。
2.水與草的交會處。字又作“湄”。《釋名·釋水》:“湄,眉也。臨水如眉
臨目也。”
子:籽(王力1982 指出,“籽”是晚起的字,見於清代,字本作“子”)。
牙:芽(字本作“牙”)王力(1982):“嬰孩初生無牙,生數月始出牙,故牙齒
的‘牙’引申爲萌牙的‘牙’,後人加艸爲‘芽’”。
府:腑
藏:髒
沒,沈沒;歿,死亡。
以上例子可看作是一詞多義模式中的義項獨立爲詞的結果。
寤,睡醒:悟,覺醒。
以上例中的前一個字在現代基本已經不用。
也有個別在語音形式上也有變化的,如:
捧,雙手捧著;奉,奉承,供奉。
很多由隱喻造成的引申義可以與本義並存,並不與本義形成競爭關係。但也有一些隱喻産生的引申義最後發展爲基本義,而本義逐漸廢棄不用。如:
關鍵 1 門閂或類似門閂的東西。
2 事物最關緊要的部分。
除了在詞義引申中起重要作用,從漢語同源詞的研究中還可看出,隱喻在原生的理據相同的同源詞的形成中也起著關鍵作用。隱喻方式可能是上古時代人們組織概念網路的一個重要依據。
很多同源詞反映的是詞與詞之間語源上原生性的聯繫。即用同一語音形式來給具有相似性的一組概念命名。被給予相同或相近語音編碼的一組詞往往具有某種外部直觀的相似性。
這可以看作是隱喻,但並不是那種語言學家討論比較多的從較爲具體的認知域到較爲抽象的認知域的投射,而是從一個具體的認知域到另一個同樣是具體驗的不同的認知域的投射。
比如王力(1982)提到:“句(勾)”是曲的意思,曲鈎爲“鈎”,曲木爲“枸”,軛下曲者爲“軥”,曲竹捕魚具爲“笱”等。
正如張博(2003:116)指出的,上古漢語的構詞理據多爲易於感知的狀態特徵。
可見,上古漢語的使用者是通過感知上的相似來編織概念網路。這個最初的概念網路可通過隱喻豐富意義,這就好比使網路上的每一個結點增大,擴大包容量,並通過轉喻的方式向外擴張,創造新的結點,即産生新詞。
轉喻在詞義的引申分化以及新詞的産生中所起的作用相對於隱喻來講更大。
由轉喻形成的新義可以與舊義同形,如:
《說文通訓定聲》:按自飲曰飲,飲人亦曰飲,所飲之物即曰飲。
“自飲”“飲人”“所飲之物”這三個意義之間就是轉喻關係。這種轉喻關係用同一字形來表達。
再如以下同源詞之間語音相同,在意義上也是轉喻關係,如:
魚:漁
禽:擒
昏:婚
右:佑
耳:刵
但是形同的一般音有變,音同的一般形有變,音形俱同的比較少。這就是說,轉
喻義很少與原義以一詞多義的形式出現,在一般情況下都要有標記。也就是說,轉喻義都有可能被識別爲一個新詞。
語音方面的改變,有時是聲母變,有時是韻母變,有時是聲調變。如:
臭:嗅(聲母變)
賄:貨(韻母變)
好(上):好(去)(聲調變)
有些由轉喻所形成的詞義最初可能是一詞多義的形式,但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會分化爲不同的詞,如“湯”和“燙”。英語中的window 的詞源義與wind 相關,指進風的眼(源自斯堪的那維亞語windwuga<vinder 風+auga 眼)。Window 和wind 之間也是轉喻關係。
各語言中用派生詞法表達的意義變化一般也都是轉喻性的,比如英語用加尾碼-er 的方式表示施事者,施事者與動作之間就是轉喻關係。隱喻義一般都不會用詞法手段來表達。
轉喻義和本義之間如果不分化爲兩個詞,那麽這兩個意義往往會産生競爭,競爭的結果,有可能是轉喻義取代本義成爲基本義,而本義則逐漸消亡。
如“兵”,本義是武器,後來通過轉喻,産生出“士兵”的意思,本義逐漸很少被使用了。
與原義在形式上完全相同、沒有産生分化的轉喻義往往只是在語境中存在而沒有轉化而固有的辭彙意義。
如“白宮”指美國政府,這只是在語境中存在,並未固化成詞語的辭彙義。古漢語中的詞類活用多爲句法性轉喻,未造成辭彙性的轉類。
如“汝欲吳王我乎”中“吳王”未固化爲動詞,“披堅執銳”中的“堅”和“銳”未固化爲名詞。
3、動源名還是名源動?
動詞和名詞到底哪一個更古老?很多語言中都有動詞和名詞之間具有詞法關係的現象。是名源動還是動源名?
梵語語法學家有一個詞根理論(Root Theory),認爲所有的詞最初都來源於動詞詞根。(Harris & Campbell 1995)從漢語的同源詞中可以看出,更多的是動詞源於名詞。從字形上看,很多名詞是獨體字,相應的動詞是在名詞的基礎上增加偏旁造出的。如:
家:嫁 扇:搧 勺:酌 田:佃 風:諷 咽:嚥 道:導 腋:掖(王力1982)
扣,是“口”的動詞用法,以器皿之口倒置爲“扣”。(董爲光2004)
羅:罹(俞敏1980)
從名轉動的語義類型來看,最常見的是用工具來轉指用其完成的行爲,如:扇、搧,背、負,蹄、踢,藥、療。
也有用名詞表示以名詞爲受事的動作的,如:魚、漁,禽、擒等。
當然,由動詞轉化爲名詞的也有不少,如:
坐:座 奉:俸 嬰:纓 隔:膈 虐:瘧 告:誥 教:校 勞:癆
從語義類型上看,名源動從同源詞的角度看很少是由動作來轉指動作的參與者,而往往是動作作爲一種功能或特性來轉指主體或與之有關的工具、場所。
當然,在漢語辭彙雙音化之後,很多雙音動詞都引申出了指稱其動作參與者的名詞用法。
我們認爲,從實際情況看,漢語中動源名還是名源動的實例都存在。
在動源名的例子中,名是更常見的、具體的佔據三維的名物,
而在名源動的例子中,名是較爲抽象的、不佔據三維空間的名詞或雖然具體,但並不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使用率高的名物。
可能在最初既有一些表示常見名物的名詞,也有一些表示經常出現的動作行爲的詞。這些基本的名詞和動詞是原生的詞根,在其基礎上派生語言中其他的詞。
我們猜想,和印歐語相比,從語源的角度看,漢語中名詞的地位可能更爲重要。
沈家煊(2008)認爲,漢語的動詞是名詞的一個次類。所以漢語在句子組織上更重視意合。
但印歐語動詞的地位更基本,所以以動詞爲核心來組織句法,句子在組織上更重視形合,句法規則明晰。當然這不是一個容易證明的命題。
4、同源詞聲韻表義功能的分工以及音義關聯的傾向性
同源詞中所反映出的音義差別與西方所謂的morphology 的性質相差比較大。
趙元任(Chao1968:10)說,“語音改變作爲一種語法手段,已經不積極應用了。例如“長chang”和“長zhang”,‘刷shua’和‘涮shuan’。……僅僅語音不同,不是語音改變。
例如‘包’和‘跑’,‘倉’和‘槍’。
但是,即令是真正的語音改變,在實用上也是當作語音不同的辭彙事實來處理較爲方便。因爲歸納不出幾條簡單的規律。
例如我們不能說去聲使名詞變爲動詞。你也許從‘種’(名)、‘種’(動)之類的例子獲得這樣一個印象,可是立刻會想到相反的情況,如‘處’(動)、‘處’(名)。這種情況不僅現代漢語如此,古代也是如此。”
如果要確定詞法關係,必須找到嚴格的音義對應,即語音的某一改變對應于詞法意義的改變,但古漢語的同源詞很多反映的都是離散的辭彙性的關聯,而不是具有能産性的詞法模式。但我們不排除在上古漢語中可能存在一些嚴格的詞法模式,但這有待於更多材料的證明。
觀察漢語的同源詞,我們可以發現在意義變化時語音改變模式的一些傾向。
當派生詞與源詞的語義類別沒有明顯差別時,僅聲母改變,韻母保持不變。
但是當語義類別有比較大的變化時,聲母不變,韻母變。
比如,“潮”得名於“朝”,與“朝”韻母相同,但聲母變化,由端母變爲定母。因爲“潮”指一種名物,而“朝”則是指時間,二者所屬的類別已經發生了變化。
涉及詞類改變的一些同源形式也往往是聲母有別,尤其是名詞變爲動詞、形容詞變爲名詞時更爲明顯。如(例子引自王力1982):
肩kyan 掮 gian
坎kham 陷heam
帚tjiu 掃su(照心鄰紐,疊韻)
黑xk 墨mk
卑pie 婢bie
如果語義類別未變,就只變化韻母,
如:“柔”與“弱”,二者都是形容詞,性質相關,因此聲母相同,韻母不同,幽沃旁對轉。
“溢、盈”都是不及物動詞,性質相關,也是聲同而韻異,是錫耕對轉。
“帛”和“幤”都是名詞,帛是總稱,“幤”是束帛,二者也是聲同韻異,是鐸月通轉。
這表明韻母與語義的具體特徵相關聯,而聲母與語義類相關聯。
當然,這裏也不是完全沒有例外,這種語義關聯只能看作一種比較強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