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能做之事
你赞赏什么行为?以下两种回答颇不相同:
“那还用说,那当然是秉持道义、务求公正的行为!”
“在所处条件下能够做到且效果最好的行为。”
与大义凛然的第一个回答比较,后一回答显得过于低调平淡,颇有些机会主义或实用主义的意味,没法子激励人心。然而,理性地看来,恰好后一回答是更可取的。
求和种种
如果你路遇劫匪,估量自己并无抗拒之力,那么你多半会适度地满足劫匪的要求,以期尽快脱身。这在大多数人看来是无可指责的。
但如果一个国家遇到类似的事情,当政者在决定和与战时就远没有如此简单,他不仅要仔细判定所作选择的战略后果,也要考虑到舆情民意的反应。在很多情况下,选择求和是更艰难的决定。
历史上,主和的当政者罕能逃过当代乃至后世的骂名。
秦桧夫妇的铁身,跪于西湖畔请罪已有一千年之久,至今仍不能得到世人的宽恕,这对人们的警示已够昭明了。几乎没有人细想,秦桧真的该当此罪吗?如果不考虑陷岳飞于冤狱一事——其实那不过是替皇帝老儿受过而已——,仅就对已据有中原的金国主和而言,千秋功罪是很值得重新评说的。
鸦片战争中主持和议的大臣琦善、耆英等,还来不及承受千年骂名,但也未能洗脱汉奸——准确地说应该是满奸——的污垢。或许,即使在多少年后的教科书中,他们仍然将作为大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反衬出现。未来年代的人们大概无暇细想,抛开君命难违这一层不说,琦善等在当时是否还能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甲午战败无疑将是中华民族永久的耻辱,当时的主帅李鸿章自然罪责难逃。但李鸿章更因签订《马关条约》(1895)而背负汉奸之名,却未必不可再议:如果当时李鸿章在谈判桌上大义凛然,拒绝和议,愤然离席而去,大清帝国所面对的后果将是什么呢?
1870年的普法战争,一方面造就了空前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另一方面则在法国留下了一个“卖国政府”。拿破仑时代大胜普鲁士的那份无上荣光,被梯也尔政府的屈辱求和一扫而空,要骄傲的法兰西在当时原谅梯也尔确实也难。但在当时的局面下,在法兰西能找到一个体面地收拾残局的大英雄吗?
敢将导弹运入古巴,摆放在强大对手美国的家门口,赫鲁晓夫的勇气不可谓不大。但在1962年,在肯尼迪总统的最后通牒下,赫鲁晓夫还是退缩了:他下令从古巴撤出全部导弹!
当满载导弹的苏联军舰在美军监视之下驶离古巴之际,全世界在核大战威胁的恐怖下紧绷的神经总算松弛了。无论在东西方,都没有多少人乘机讥刺赫鲁晓夫屈膝投降,唯有中国的反修斗士不失时机地给赫鲁晓夫戴上一顶“投降派”的帽子。在当时的形势下,赫鲁晓夫果然能够赖在古巴不撤,静候肯尼迪掀动核按钮吗?
因主和而负卖国罪名者,古今中外不可胜计,难以尽述。在历史的法庭上,值得重审这些人的案子吗?今天的审视者,将如何评判那些陈年旧案呢?
一部分人会秉持道义的理由:凡违背正义的决策都是不可接受的。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尊严,从来都是最大的正义。以此标准衡量,秦桧、琦善、李鸿章、梯也尔、赫鲁晓夫等就是卖国贼无疑了。另一部分人则以情势判断为准绳:在无望取胜的条件下,争得可能的最好结局,就是理智的决策。
问题的焦点在于,如何判定主和者真的“无望取胜”呢?在远离历史现场的今天,人们既拥有足够多的资讯,也具有较充分的冷静客观,已不难作出较准确的判断了。例如,你真能相信:羸弱偏安的南宋小朝廷能够战胜强悍的女真铁骑,北定中原?老朽颟顸的清帝国能够驱除船坚炮利的英国舰队?甲午战败后千疮百孔的清帝国,还能奋起一战,反败为胜?拿破仑三世被俘后的法兰西,还有力量与空前强大的德意志再作较量?赫鲁晓夫可以坚持不撤导弹,也能避免核大战或者在核大战中完胜不败?——你真能相信这些都是可能的吗?无论公众如何判断,大多数历史学家大概不会这样认为。既然如此,坚持一种毫无希望的选择,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历史所启迪的智慧只能是:做你所能做的事!为所不能为,不论如何有正义之名,都并非智者的选择。
保守的改革者
改革者所面对的情势不那么刀光剑影,但决策之艰难未必稍欠于和与战的选择。不少雄韬伟略的改革者,因深谋远虑、谨慎决策而背负保守的骂名。
康有为无疑是光绪年间最风光的人物。今天还有不少人记住他,可能不是因为他是戊戌变法的功臣,而是因为他是不合时宜的保皇派罪人。康梁的变法主张——其核心思想是君主立宪——已被后来的革命洪流冲毁净尽,康有为还能算一个可敬的改革者吗?
罗斯福无疑是20世纪最负盛名的世界领袖,他之所以被人们崇敬,既因为其在二战中的主导作用,也因为他的广受颂扬的新政。没有人否认罗斯福作为西方世界主要改革者的地位,但不少人质疑他的新政的种种局限,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批评尤其严厉:新政不过是稍稍修补资本主义的漏洞而已,丝毫不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缺陷。如此看来,罗斯福的事业似乎气魄还不够大,他还能算一个伟大的改革者吗?
赫鲁晓夫曾经是中国政界最厌恶的人物,但这并不妨碍世界的主流舆论认可他为不可多得的勇敢改革者,是持续半个世纪的革除苏联弊政这一伟大运动的真正发起人。但与后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的所作所为相比较,赫鲁晓夫那些仅触及皮毛的改革,似乎微不足道。他也太小心谨慎了些,还能算一个杰出的改革者吗?
与赫鲁晓夫比较,一度成为中国领袖的华国锋似乎更难称为改革者了:他坚守“两个凡是”,津津乐道“你办事,我放心”,迟迟不为文革受难者平反。但是,毕竟是他甘冒风险一举清除了极左的文革派,他实际上结束了文革祸害,开启了迈向正常国家的艰难转折,让封闭多年的国家开始面向世界。这些不正是一个杰出的改革者所应做的吗?
“改革”或许是当代人最欣赏的一个词。但真正完美的改革者少之又少,如果不是根本没有的话。几乎每个改革者都会被一些人指责为过于保守,又被另一些人指责为过于激进,这怎不叫人进退失据、踟蹰不前呢?在社会转折的狂热气氛中,通常“过于保守”的指责呼声更高。评判这种指责是否合理的关键在于:改革者的目标恰好是他所能做到的吗?或者,在当时条件下,他的改革取向是最佳的吗?
在民权呼声渐高的年代,康有为仍不愿废了他至死效忠的皇帝的尊位,很难不被斥为保守派。但是,从后来的民国或共和国表现之恶劣看来,康有为的君主立宪方案未必不是一个更可取的主张,可惜已没了一试的机会。
那些期望罗斯福的新政真正为进入社会主义铺平道路的人,未免太想入非非了,你想让美国成为另一个苏联吗?如果是那样,就会有更多的人宁愿罗斯福倾向保守了;否则,美国势必也将有它的1991!
看看赫鲁晓夫有那样多的同僚拼命反对其改革,而且最终废黜了他,你就明白,身处1950年代的赫鲁晓夫不仅不保守,实际上简直有点冒险了。
华国锋本来是一个厚道本分之人,在生死关头义无反顾,毅然主导了翦除四凶的那次历史性事变,已经勉为其难了。在那个头脑普遍僵化的年头,你还能要求他有什么更惊人之举?如此看来,康有为、罗斯福、赫鲁晓夫、华国锋并不保守;如果说他们保守,那也是一种合理的、必要的保守,他们只不过是做了在所处条件下所能做的事。对于这样的“保守改革者”,人们能够苛责吗?
乌克兰的选择
为申述本文的观点,目前的乌克兰或许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即使是最乐观的人,现在也难免忧虑乌克兰的前途了,它会陷入永无休止的内乱吗?
谁都知道俄罗斯从来都是虎狼之国,在欺凌蚕食它的近邻时绝不心慈手软;它吞并克里米亚、挑起东乌克兰叛乱,没有任何道义可言。谁都知道,几百年来饱受俄罗斯欺凌的乌克兰,好不容易趁苏联解体之机获得了独立,仍然不得不外抗强邻,在道义上不输俄罗斯一分一毫。
然而,再强的道义优势,也不能成为决策的依据。别忘了,今日之地球,仍然是以利益为第一考虑的世界。不以物质力量为后盾的道义力量,不足以解决当代任何重大的问题。
那么,不输道义的乌克兰,所能依仗的物质力量何在?它有武装力量抵挡世界第二号强大军队,哪怕抗击一周以上吗?它有俄罗斯之外的可靠经济伙伴吗?它有不依赖于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吗?它有在交战状况下足以养活自己人民的雄厚财源吗?如果没有这些东西,能够指望西方盟友提供这一切吗?——如果所有这一切全不具备,徒有对抗强邻的万丈雄心,谈什么抗拒俄罗斯!不宜抗拒那头粗暴的北极熊,非不义也,实不能也。
欧洲在其最辉煌的岁月中,都未真正制服过北极熊。欧洲已足足享受了70年的和平,今天已不再是一个勇武的巨人,既无战争的武备,更无打仗的意愿,它能为了远在欧洲核心地带之外的乌克兰冒险与俄罗斯一战吗?
对于不遵守国际规则的俄罗斯的肆意妄行,欧洲不能不怒火中烧,它已在俄罗斯面前晃动了拳头,宣布了若干制裁措施——这已是它所能打出的最大的牌了,它还能真的将伸出的拳头打到北极熊头上去吗?至于当之无愧的世界头号军事巨人美国,无疑比欧洲有大得多的战略优势,而且是俄罗斯的宿敌,是第一个不希望俄罗斯占到便宜的国家。即便如此,目下它也不愿意与俄罗斯直接对抗,其所肩负的国际义务也实在太多了,它的力量并不是无限的。
总之,乌克兰内无实力,外无真正能够且愿意使上劲的盟友。对于乌克兰面临的这种险恶情势,俄罗斯人全看在眼里,理性的局外观察者亦洞若观火,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也未必不心知肚明。
面对如此无情的现实,一个理智的小国领袖该做什么,也就清楚了。形势不仅比人强,而且也比如日月高悬的道义强!波罗申科固然不应做卖国贼,但也不必做拼命三郎。他不是能够逞匹夫之勇的好汉一条,而是肩负5000万人命运的一国元首。他还拥有一片活动空间,充分施展自己的智慧与俄罗斯周旋。他应该在西方与俄罗斯之间,找到一条让乌克兰安身立命的生存之道。
世界历史上,有足够多的小国,凭借高超的外交技巧游刃于强国之间,其中的智慧足可借鉴。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必要地刺激北极熊,绝非求生之道;急于加入北约,尤其不可取,况且也不现实,那只能促使俄罗斯决然关上和解的大门。冒着被国人误解的危险,与从无信义可言的北极熊妥协,对于任何不失尊严的人都会是极其痛苦的事情。但波罗申科就得干这件痛苦之事。政治家无权计较这些,为了国家,他必须做自己能做之事。
就事理而言,乌克兰的出路只能如此。至于波罗申科是否也这样看,或者是否有勇气作出决断,则非我所知也。
做能做之事
前述的事例表明,在涉及和平与改革的问题上,政治家的选择原则其实很简单:做你能做之事。这既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伦理,它体现了对公众与历史的真诚与责任感。
“能做之事”意指这样的事情:在所处条件下能够做成之事;或者,在所处条件下能够达到最佳结局的事情。判定什么是能做之事,当然需要智慧与经验。
能做之事未必是决策者内心最想做的事情。华国锋在1977年选择了让邓小平复出,这在当时不失为一种理性的决策,其内心是否乐意如此,则大可置疑。能做之事也未必是当下很得人心的事情。梯也尔在1871年接受了德国人苛刻的和平条件,在当时实在是别无选择,但还是被热血沸腾的法兰西男儿骂为卖国贼,而且激起了“巴黎公社”之变。
在违背个人或公众意愿的情况下,理智地做能做之事,往往要承受巨大的内心痛苦。这可以说是理智的政治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不愿付出这种代价的人,则很可能选择违背理性,取悦世人,随波逐流,不惜酿成社会恶果。倘若如此,有后世人可以效法的价值可言吗?
能做之事也未必符合决策者的长期目标。例如,在1980年代初期,中国改革者只能选定一个较低的目标:建立受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可以理解,至少在那些最有远见的改革者心中,经济改革的最终目标应当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但这既不是当时能做之事,也不是当时能说之事。只是在十年之后,在历史性的邓小平南巡之后,市场经济才明确写在改革的旗帜上。选定一个暂时的、随时准备超越的目标作为当下的能做之事,而将最终目标秘而不宣,这该需要多么深沉的韬晦功夫啊。
能做之事未必肯定实际做成。所谓能做,仅指当主要条件具备时,所选择的目标原则上能够达到。但并不排除,由于某种偶然的次要因素的干扰,致使预定目标最终未能实现。例如,戊戌变法纵然失败了,但并无理由认为它绝不可能成功;实际上,仅仅7年之后的新一轮变法,甚至比康梁走得更远。戊戌之败,主要与某些细节上的处置失当有关。因此,仍然可以说,康梁选择了他们的能做之事。
做能做之事,平凡而现实,每天都被无数人士践行着,并不需要特别的哲学包装。如果一定要贴上某种标签,不妨唤作保守主义或现实主义,这都不是什么光辉夺目的名词。
我们身处一个躁动不安的时代,有较多的人奉行一种保守的哲学,不失为一件幸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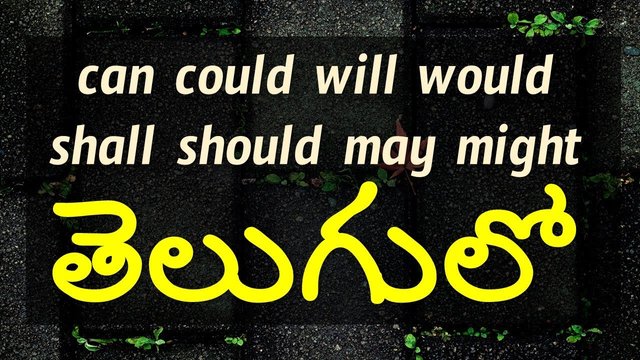
帅哥/美女!想来玩目前STEEM上最火爆的drugwars游戏吗?还在等待什么?赶快加入战斗吧!drugwars.io倘若你想让我隐形,请回复“取消”。
@tipu curate 5
Upvoted 👌 (Mana: 0/10)